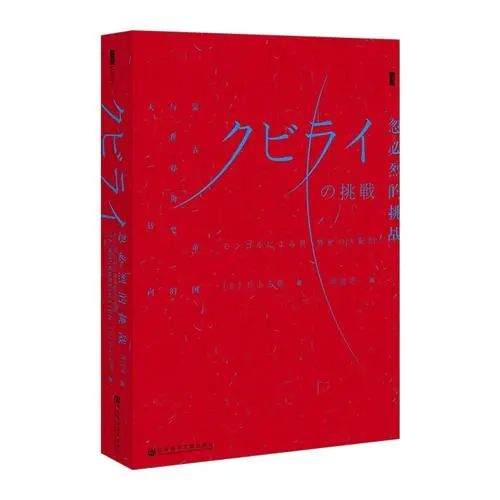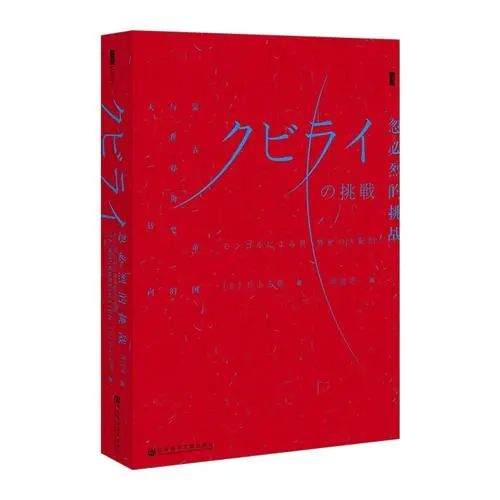newrover(漫游)
https://mp.weixin.qq.com/s/VgcCcNTGAuVDQR1XvSbnmQ
“臭公知”发微
最近这段时间,我这小号上突然涌来很多攻击谩骂的留言,很多稿子他们其实骂无可骂,留言都是直奔着扣帽子去的。比如某一篇谈西游记的稿子底下,有人就直接这么写:“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就是个臭公知。”这个留言本身,当然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但“臭公知”这个用词,倒是勾起了我的不少儿时的回忆。我祖父是个物理教师(说话间老人家刚好走了四年了),经历过特殊年代的那种人,他晚年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已经显著提升了,被加了“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尊号。不过可能是年轻时候挨批斗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晚年还是喜欢自嘲的说自己是“臭老九”。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仨字儿的意思,上中学时才听说,据说元朝的时候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读书人地位比娼妓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所以叫“臭老九”。可是大学的时候我读了历史系,却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正如日本蒙元史学家衫山正明所说,今日中国民间对蒙元形象的很多传说,其实是高度失真的,历史上真实的蒙元帝国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种“蒙古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黑暗。至少像“读书人是臭老九”这种政治贱民划分方式,我们在元朝现存的官方典章制度中是查不到的,正史更是无载。那这东西从哪来的呢?郑思肖生于在宋末元初,他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大宋经历崖山之役,就已经亡了。郑思肖不愿意出仕元官,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靠卖画为生,他画兰花是一绝,比他更有名气的书画家赵孟頫都曾来找他求过画,可是郑思肖嫌弃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居然屈身事元,就躲着拒不见客,还留下一句“头可断,兰万不可得!”弄得赵孟頫下不来台。按说这么一个铁了心要做前朝遗臣的顽固分子,敢这么对新朝给脸不要,放在明清时代,分分钟那都是抄家灭族的节奏。但好在蒙元时代的朝廷虽然野蛮,却还没有那么小心眼,郑思肖居然开开心心在大元又活了40多年,七十好几时才寿终正寝。他闭眼的时候朱元璋都快出生了。晚年的郑思肖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著作,留下一本《心史》,这本书里面全是什么《陷虏歌》《大义集》之类的东西,对着元朝廷骑脸输出,其中有一段就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如前所述,这个都不属于谤讪朝政了,这属于直接造谣,人家元朝从来出过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什么叫“一官”“九儒”?你们儒生读了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讨个官做么?你看人家赵孟頫,同样是读书人,只要跪的下,舔的好,乐于歌颂新朝雅政,那官是可以做的很大的,晚年赵孟頫加荣禄大夫,死后获赠魏国公。我大元很尊重你们读书人啊!可是郑思肖却不管,他硬要这么写,那意思大约是觉得,你们元朝对我们这些不愿意和你们合作的大宋遗臣不够尊重。这话倒也对,忽必烈搞的那套“蒙古自由主义”,说到底其实还是国营外贸企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感觉,对民间只是赋税轻一些,财富是没有藏富于民的。像郑思肖这种坚持不愿意出来做官,“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隐士,后半生注定过得比较穷困潦倒。所以郑思肖老爷子其实是在抱怨一件中国帝制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你身为读书人,不想跪下颂圣、当皇帝的附庸,还想让皇帝尊重你,这在古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当然,宋朝养士三百年,可能确实把知识分子养到了一个临近觉醒的门槛上。你看欧洲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郑思肖的同行米开朗基罗,就一边对着教皇骑脸输出,一边还让教皇给他发高薪。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一边写《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揭了整个教廷的老底,一边居然还在教廷出资办的神学院任教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时代确实就来了,而紧接着则是人类近代大门的隆隆开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这一辈子,是在这种变革之后才活的有那么点意思的。但你不能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大元皇帝,就算是出奇好脾气的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人家那个“仁”也只是说他在古代中国一众小心眼的皇帝中稍微大度那么一点点,论人文修养和艺术品味,人家一个草原上“套马汉子”出身的朴实牧民,你到底在期待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变化,其实是有明暗两条曲线的,明的一条曲线是如果你愿意考科举、走仕途、进入体制内,天天跪下称颂皇恩,那你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不变。明清为官环境相比前代虽然也惨了一点,但好歹比作社会上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强一些。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是“读书高”,是考上科举高,能被皇上收下当狗高。暗线则是想独立于朝廷之外。那就比较惨了,宋以前读书人如果家里有地,可能还有点当隐士的自由,元代已经如郑思肖所言,近似臭老九,可大元皇帝好歹还让你或者。你看看后世的明清,我觉得郑老爷子就应该知足——他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我大清,都不用提他公开造谣、污蔑朝廷,就冲他敢写“鞑法”这个敏感词,参照乾隆爷办“字贯案”的成例,让你子孙男的凌迟、女眷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再开棺戮尸、挫骨扬灰、骨灰扬上七七四十九遍都够了。你还敢抱怨你为什么是臭老九?而如果我们给不想跪的读书人这条地位下行曲线找一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曲线的起点远在先秦那里。先秦时代的韩非,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就写文章给国君出主意,说现在社会上有“黑五类”(五蠹)啊!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吸血鬼,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君权的太阳东升!哪五种人呢?韩非说,他们是学者(研究学问的人)、言谈者(在民间交头接耳、搞舆论的人)、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敢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做生意和凭手艺混饭吃的人)。言外之意,就是韩非个这疯子,不仅觉得读书人有罪,而且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自然职业在他眼中都是“没用”而且“有罪”的。那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职业是有用的呢?韩非说——耕战,也就是种田与打仗,秦国老百姓可以在地里当韭菜和上战场当炮灰之间完成人生的二元切换么!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古代版法西斯理论,但恐怖的是,秦国居然真的执行了韩非这疯子的狂想。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这话送给最终在自己梦想的体系中没得好死的韩非先生非常贴切。当然,可能韩非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或言谈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就是被某个欣赏他的君王收下当狗。可是韩非给秦王朝制定的这套社会观,在有效之余却是有两个致命问题。问题一,是这是一套大秦所有贵族、老百姓都一起受损,只有君主一个人得利的系统。因为韩非说的很清楚,民众的任务就是耕战,在平时的韭菜和战时的炮灰之间来回做二元切换,其他所有不符合君王利益的职业都是非法的、有原罪的,民众在这个体系下生活,肯定不开心,甚至侥幸在内卷中获胜的官员也不开心,商鞅、韩非这帮始作俑者最后都喜闻乐见的作法自毙了,甚至范雎、吕不韦、李斯们做到丞相也不能得好死。最后唯一活的比较爽的,可能就只有秦王一人。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秦二世胡亥这小子其实也算个聪明人,因为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吾既已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小爷我既然当了这个皇帝,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穷奢极欲活个爽啊!要不然法家搞那么些改革为了啥?我爹一扫六合又为了谁?大家都活的苦哈哈、紧张兮兮,不就是为了皇帝能自由快活么?这话其实聊的很通透,专为君主一人谋划的法家,想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这个。可是胡亥又有另一段名言,就是等秦制这一套最终弄得天下鼎沸、秦国二世而亡的时候,当宦官走上前来,要杀他,他可怜兮兮的开始求饶。说“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不可以?”“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是南朝刘宋的末帝被杀死前发出的千古悲鸣,这孩子被从床底拽出来杀掉前只有十三岁。法家给古代中国打造的这套帝制系统,明面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为皇权服务的螺丝钉,皇帝是唯一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皇帝和其后代也没办法在这个体系中永久,长期的受益。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之频仍、皇族在王朝覆灭之后下场之惨(而且是越来越惨)是个整体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法家的这套黑色乌托邦,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最终并不有利于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当然喜欢看古代王朝地图开疆的意淫者除外。这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短期的高效之后,长期看却是窒息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的。因为你一口气把独立知识分子(学者、言谈者)、民间非政府武装(游侠)和工商业者(工商之民),一口气全打成了黑五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自由基”全部消失了,于是社会就只能跟着独大的皇权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反复治乱循环。而在近代,我们会发现欧洲之所以能完成近代化,恰恰离不开这些自由基。非官员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启了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更重要的理念革命,民间的“游侠”如哥伦布、皮萨罗、库克们则杨帆冒险、开拓,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同样让韩非痛恨的工商之民,则创造了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一骑绝尘的将其他文明甩在身后。一切的结果,是等到1840年以后,等洋人带着近代革命的坚船利炮、马克沁水冷机枪打上门来的时候,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只有惊叹洋人器物“变怪神奇”的份儿。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这种悬殊的差距,其实一场两千年慢性中毒的总发作。从五蠹,到臭老九、再到臭公知,有些国人总喜欢把从事一些职业的人看成天生低贱、甚至有罪的贱民。其实这个事情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不仅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口中是“臭”的、“臭”这个字儿几乎可以被他们用来瞧不起一切行当,臭教书的、臭江湖郎中、臭打工的、臭外地的(乃至外国的),甚至臭资本家(这更不得了,在有些人口中得挂路灯)。一个臭字几乎可以让持此论者睥睨一切行当——一如当年的韩非一样。而这种瞧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知,就是有大量的人真的觉得这些职业取消掉比存在对他们更好。当然,唯独一种职业他们不敢以臭字贯之,那就是考公务员,进体制内。“臭当官的”这个词儿这帮人估计不敢轻易喊,因为他们知道这惹麻烦,破坏了他们的顺民形象。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考公考编,进体制内是丈母娘们唯一认可的女婿职业,因为在一个普遍持有这种思想遗毒的社会中,其他职业都被认为是不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取消的。所以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但我还是会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写作,不仅是我自己的职业,更是帮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从一种轮回了数千年的鬼打墙中解脱。“臭公知”“臭老九”,若这苦难与艰辛是必须的,若这付出乃至牺牲是值得的,我将以此为荣。本来想起题目叫《“臭公知”发微》,其实更准确一些。但我怕这个题目有点掉书袋,有些朋友看不懂,想了想,还是用了现在这个——您看,其实我是个愿意在掉书袋和通俗易懂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的人。今天的音乐是《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首很好听的德国哲思古曲。选它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传统就起源在法德,法国我写过了,本来今天想再说说德国,可惜今天文章聊不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本书,《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愿意读,肯定比听我讲更透彻。另外,如您所见,谣诼越来越多,写作越来越难,请您和您值得的朋友关注我的号,别走散。不管怎样,感谢所有读完的朋友,愿您喜欢本文,我为你们而写作。晚安。
(#16294919@0)
Last Updated: 12:05